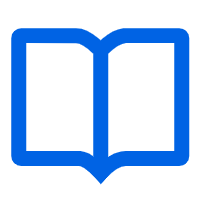中国改革向何处去?
我是干社会工作的,对经济了解有限,但改开40年总体方向是对的(个别决策有错误),所以经济才快速发展。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先富和后富的问题,北上广深和边远地区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深化体制改革,走向共同富裕。
但如何深化?向何处深化?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我简单说几点看法吧。
1、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这包括电信业、电力、石油、铁路民航、医疗教育等,这些领域过去或现有市场垄断、行政垄断或地区封锁的情况,应该放开,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2、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怎么进行市场化交易,实现价格发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3、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中央政府应该放什么权给地方?地方政府应该放什么权给基层政权和组织?如何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匹配?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议题。同时,加强宏观调控,避免市场失灵,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也是重要内容。
4、收入分配改革。这个不用多说,继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实现居民收入的提升。
5、金融体系改革。这是个大话题,直接关系到宏观稳定和经济发展。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跨境资本管制都是很重要的内容。
6、生态文明体制建设。这个也不多说,环境恶化已经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7、党的建设。包括执政党能力建设、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等。
政治改革的艰难之处,就在于改革者的决策往往处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尴尬位置。改革者的责任就在于,尽最大可能设计一种能够把风险和成本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的改革方案,尽最大可能去实现最有可能实现的目标,以期取得最大的实际效果,为今后的发展奠定更宽广的基础。
任何国家的政治改革都是具有本国特色的。有的国家是“革命+改良”,有的国家是“改良”。就“改良”而言,有的是从政治开始破题,有的却是先从经济入手。中国就属于后者,先从经济改革入手来推动政治改革。这种改革方式的好处是降低了风险,但也使政治改革的难度加大。因为经济改革有很强的溢出效应,比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权力的约束和民主的发展,但它也会产生一些阻碍政治改革发展的消极因素,比如社会分化,利益集团形成和寻租行为的增多。
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在经济改革产生了大量“制度外民主”之后才开始启动的。这使中国的政治改革一开始就面临很大的压力。它不仅要解决政治制度的问题,而且要解决社会自身发展起来的大量的民主诉求与现有的民主制度难以有效承载这些民主诉求之间的矛盾,要努力把制度外的民主尽可能地纳入制度的轨道之中,把“制度病”转变为“制度内”消化掉的问题。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个需要解决更多问题的改革,是要求更高的改革。
中国在经济改革中,从试点取得经验之后就很快全面地推进了。政治改革同样采取了试点,如扩大基层民主的试点就有许多,但政治改革从试点到全面推进的转化是不容易的,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更敏感,一些具有“爆炸性”的改革还不能一步到位,只能“小步”前行摸索。其次,政治改革的“溢出效应”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更多,也更难“消化”。
但这并不等于说,政治改革没有实质性推进。比如,政府的公共性和公信力问题、官员的问责制、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的提出、干部的任用制度的改革以及城乡选举制度的改革,甚至包括政府机构改革的尝试,都表明政治改革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当然,与人们的期望还是有距离的,有的问题还相当突出,如“吏治”问题。其实,中国的“吏治”问题主要不在于干部素质不行(虽然腐败严重化的现象和一些腐败大案、要案确实使人们对干部队伍的素质产生了怀疑),而在于权力的约束问题。就一般干部而言,即使没有那么高的素质,“吏治”也不会坏到无法挽救的地步。
那么,中国政治改革应当向何处去?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们只在这里从总体上说一说。第一,政治改革应当与经济发展协调推进,而不是等待经济发展水平达到很高才进行。第二,政治改革需要大胆地试验与小心地推进相统一。第三,政治改革需要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特别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和政府内部的关系,因此既需要有改革魄力,又要具备相当的协调能力。第四,政治改革既要与经济改革同步,但也要从政治改革自身的规律出发,从群众最容易接受的问题入手,并抓住突破口来推进。第五,政治改革的措施,要力求稳扎稳打,以期取得实际效果,取得群众的信任,这样就能为继续推进政治改革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