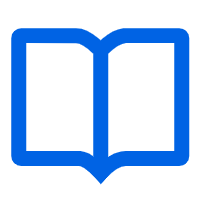杍在五行中属什么?
“杍”字,《说文解字》里归入“木部”[1]。 《康熙字典》注释【補】字: 《說文》作樸字;作樹之屬。又作株、主。 《集韻》作柤,或作楂。
《正韻》作梓。 《韻補》音支。與柤同。○按《集韻》注茲雅切,當是側加切。今俗專作柤音。 《正字通》亦收补字,註云,補,梓切,古作補。 清·梁玉繩著《古今文字異義》:“補,古文作补,與鉗通。”“補,梓切。”“鉗,昨兼切。”“鉗,古文作補。” 由上可知,“補”字的字形演变过程是: 在金文中的“補”字,還有別的名稱“鉗”,可見“鉗”就是“補”的異體字。小篆把金文的形變過程徹底完成。隸書時期形成隸定楷化後的“補”字。到漢代的簡帛文字中,“補”字已經完全定型了。
我查了下《康熙字典》和《正字通》,所舉反例“俎”字,在《說文》中歸類于“木部”。這明顯是誤導。查《集韻》等字典可以證實“俎”字在近代漢語中一貫是歸類於“金部”(古文字中是歸類於“文部”)的。這是因為“俎”本為象聲詞,而後來引申為“砧板”之“砧”。《爾雅》釋“咨”為“俎聲”就表明它是一個象聲詞。《詩經·大雅·生民》“履趾踐節”,鄭玄箋:“踐,蹍也。如踐阼,踐席之意。”明代陳第著《毛詩古樂章句》:“踐,履也……《周南》‘執轡如組’、《魏風》‘駕言之難’,則此‘踐’字皆作踐踏解。”可见“踐”的字形演變也是從“攵”到“足”。“俎”的字形應該是“足”旁不是“文”旁。
五行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从当时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人们还不能科学地认知自然界各种事物的科学本质,只能够加以宏观的考察,经过抽象思维和概括得出的结论。“五行”之说,最早见于《尚书•洪范》。洪为大,范为法,就是说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中有一个大法在制约生克制化。五行之说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也称五气)形成的,这五种物质互相资生又互相制约,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所谓“生曰化,克曰裁”,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各种事物由于有这五气的生化和制约而不致平衡,生生不息,发展变化。
在五行中,“木”为东方之位,“火”为南方之位,“金”为西方之位,“水”为北方之位,而“土”则居中央,故五行又称为“五材”或“五方”。“木曰曲直”,所谓曲直,就是说木具有生发、条达、升散之象,故与春季的生发之气相应。“火曰炎上”,即火有炎热、就上向炎之象,故与夏季之热气相应。“金曰炎收”,是指金具有肃杀、收敛、沉降之象,与秋气相应。“水曰润下”,是指水有寒凉、滋润、向下、沉降之象,与冬季寒冷相应。“土曰稼穑”就是说土有利于播种养育庄稼,有生化、长养、受纳之功,故居中央。木、火、土、金、水五气分别与五脏的脾、肝、心、肺、肾的生理功能相对应。
木、火、土、金、水这五行作为物质本身而言都各有其各自的特性,但是把它们作为五行来说时,它们就不是通常所说的五种具体物质,而是五种物质其固有特性在自然界各种事物中抽象后相类归附的五个类名。古人用这五个类名来概括天下万物品性的归属。由于每一个类名下所包含的事物极多,在此列举一些与医学有关者。属木性的有:春天、东方、风、肝、胆、筋、目、爪、左、南、呼、酸味、青色、生长等;属火性的有:夏天、南方、热、心、小肠、暑、汗、舌、面、南、笑、苦味、赤色、夏长等;属土性的有:四维、长夏、湿、脾、胃、肉、口、黄色、南、思、甘味、灌溉等;属金性的有:秋天、西方、燥、肺、大肠、鼻、毛、白色、秋收等;属于水性的有:冬天、北方、寒、肾、膀胱、骨、发、黑、恐惧、喊叫、咸味、收藏等。五行学说以五行的特性及其生克关系来概括和阐释自然界以及人体中医诊断网生理病理现象,并用以指导认识和防治疾病。
“生”是指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具有辅助、促进、升发、加强、生化、生长等作用。“克”是指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具有抑制、制约、克制、战胜、消减、破坏等作用。
五行之间相生的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生我”者为“母”,“我生”者为“子”,故又称为“比化”。如肝属木,肾属水,水生木,故肝对于肾而言肝为子,肾为母。
五行之间相克的次序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我克”者为“所胜”,“克我”者为“所不胜”。如肝属木,脾属土,木克土,故肝对于脾而言,其“所胜”,脾是肝的“所不胜”。“所胜”、“所不胜”又称“所胜”、“所复”。
生中有克,克中有生,“克”可维持“生”使之不过旺而相反相成,使自然界和人体保持有序和动态平衡,即五行生克处于生克制化之中,生克平衡。“生”太过或“克”不及,导致“生”所不及而“克”也过越,事物处于紊乱无序,即五行所指的相侮。同样,“克”太过和“生”不及,也会导致